宗白华
发布时间:2022-08-19 浏览:1447次
安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境内山川雄奇、河泽灵秀,在这片灵山秀水间,孕育出众多的杰出文化人物。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光辉印记,书写了安庆的根和魂,让安庆这座古老城市的底蕴显得更为厚重,已成为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黄梅戏妇孺皆知,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科学家邓稼先、慈云桂,艺术家程长庚、严凤英,作家张恨水等等,无一不是安庆的骄傲。
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开创未来。为此,市文联策划推出了安庆历史文化名人系列推文,让大家深入了解安庆这座城市的根和魂,从安庆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新的赶考路上,守正创新,勇毅前行,奋力建设“五大宜城”、挺进“百强城市”,加快推进安庆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宗白华简介
宗白华(1897.12.22—1986.12.20),曾用名宗之櫆,字白华、伯华,哲学家、美学家、诗人。籍贯为江苏常熟虞山镇,祖籍浙江义乌。1897年生于安徽安庆小南门方宅母亲家中。母亲方淑兰,为桐城派散文家方苞之后;父亲宗嘉禄,清末举人,曾任江南商业学堂堂长、中央大学教授等职;抗金名将宗泽为其先祖。1905年,宗白华随父母亲迁居南京,入思益小学,1919年8月受聘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任编辑、主编。1920年赴德国留学,1925年回国后在南京、北京等地大学任教。曾任中华美学学会顾问和中国哲学学会理事。宗白华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被誉为“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一代美学大师”。著有《宗白华全集》及美学论文集《美学散步》、《艺境》等。
1986年12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美学大师宗白华
宗白华17岁起,接受德语学校的教育。德语里既有歌德式的浪漫情怀,又有康德式的深邃思辨,而正是这两方面把青年宗白华牢牢地吸引住了。不可否认,德语教育,对宗白华后来所从事的美学事业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尽管青年宗白华还没有对美学作专门的研究,却具备了超群的审美鉴赏能力。上海《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苏、副刊主编郭虞裳看中才20出头的宗白华,请他去编辑《学灯》副刊。
1920年5月,宗白华赴德留学,专攻美学。美学这门学科是在德国首先建立起来的,在德国学术史上,美学研究非常深入,并且形成了一贯的传统。在宗白华到德国的时候,美学研究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思辨领域,转向对审美经验作心理学上的解释。当时流行的美学理论很少是抽象的哲学思辨的结果,而更多的是现实的审美经验的总结。如果没有经历德国古典哲学对美学的深入研究,这一转向就不会有多大的意义。正是德国古典哲学在思辨领域内几乎穷尽了美学思辨所能达到的高度,思辨美学的局限才从根本上暴露无遗。思辨美学从根本上显示了研究方法同研究对象之间的矛盾,即美学运用的是纯思辨的方法,美学所研究的对象却是纯体验的审美活动。
宗白华在柏林大学的老师是著名的美学家德索(Dessoiz)。德索教授就是一位强调艺术鉴赏的美学家。在德索的影响下,宗白华十分注重对保存在欧洲各大博物馆里的艺术珍品的欣赏。正因为当时的美学十分强调艺术实践,所以宗白华在严格的哲学训练之余,仍投入时间和精力进行诗歌创作。在二三十年代风行一时的《流云小诗》中的绝大部分作品,就是宗白华在德留学期间创作的。
1952年院系调整,宗白华先生从南京大学调至北大。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是东南大学,解放后中央大学分为南京大学和南京工学院,南京工学院现又改名为东南大学),宗白华一直讲授美学和艺术学,其间还做过哲学系主任。
宗白华为何对美学和艺术情有独钟,细究起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性格上的原因;一是教育上的原因。
照宗白华自己说,他从小就爱静思和浪漫,喜欢对着天上的白云流连想。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宗白华从小就具有诗人气质。这里多少有些天生的机缘。
郭沫若的诗在四处碰壁之后,能得到宗白华的赏识,也许真的只有诗人才能真正地理解诗人。不难想象,在1919年发表郭沫若的诗需要多大的觉解和勇气。也正因为有宗白华的慧眼,有《学灯》的支持,郭沫若才能够像火山爆发似地唱出他的《天狗》和《凤凰》。
由于宗白华从不脱离艺术实践去进行不切实际的思辨,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特别有美学韵味。在三四十年代写作的《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等论文,显示出宗白华对美学尤其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体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1952年,宗白华从南京来到北大。当时的北大集中了中国美学界的三位泰斗,即邓以蛰先生、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如果说,德国是西方美学的中心,代表了西方美学研究的传统的话,北大则是中国美学的中心,形成了中国美学研究的传统。这个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北大德高望重的校长蔡元培先生那里。1917年蔡先生于任北大校长之际,即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的讲演。1921年,蔡先生率先在北大开设并亲自讲授美学课程。后来有朱光潜先生讲“文艺心理学”和“诗论”,都可以算美学课程。所以宗白华来北京以后,能感觉到一股浓厚的美学兴趣。宗白华在1959年的一封信中说:“北京美学兴趣一般颇为浓厚,目前《新建设》邀座谈会,下期可发表情况。马列学院亦拟以下半年培养美学干部,约去协助。朱先生已加入哲学系美学小组,前途颇为可观。我的第二散步,大约关于音乐和建筑,尚在准备中,未知何日动笔,因康德美学急待翻译也。”(《宗白华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当时美学的热闹情景由此可见一斑。
从《宗白华全集》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来北大之后,宗白华加紧了对西方美学史的系统研究。从《全集》中可以看到宗白华写于五六十年代间的《美学史》(纲要)和对西方美学史的一些专题研究,如文艺复兴的美学思想、德国唯理主义的美学、英国经验主义的心理分析的美学和康德美学思想评述等。宗白华翻译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可以看作他当时计划系统地进行西方美学史研究工作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60年代,宗白华同朱先生之间有了分工,朱先生负责编著西方美学史,宗白华负责主编中国美学史。由于整个中国现代美学基本上讲的是西方美学,是一批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学者在那里传播西方美学思想。因此,当时美学界在中国美学史方面的研究工作几乎是一片空白。在这种学术背景下,要写出一部成熟的中国美学史几乎不太可能。按照宗白华的看法,中国美学史的写作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对中国美学史资料有了全面深入的发掘和整理,二是对中国美学的各个部门,如绘画美学、书法美学、建筑美学、工艺美学、音乐美学等等有了较成熟的研究。而在当时这两个条件没有一个符合要求。当时有些同志想急于求成,建议一边整理资料,一边研究写作。宗白华极力反对这种意见,说“没有丰富的资料,怎么能写史?得先搞资料,踏踏实实搞上几年资料。”宗白华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他没有急于写作中国美学史,而是指导身边的几位助教,前后花了近3年时间,翻阅了北大图书馆里的大量书籍,编出了两本《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宗白华在指导编选这两本资料的同时,还整理了大量的关于绘画美学、书法美学、建筑美学、工艺美学、音乐美学方面的资料,遗憾的是这批资料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在文革中散失了。
宗白华在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之后,开始了中国美学思想的专题研究,并于60年代初给北大哲学系、中文系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中国美学史”专题讲座。在讲座中,宗白华全面、集中地讲述了中国美学史的特点和学习方法,并就先秦工艺美术和古代哲学文学中所表现的美学思想、中国古代绘画美学思想、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中国古代园林建筑艺术所表现的美学思想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深刻、精到的见解,留下来大量研究笔记。在这些笔记中常常能看到宗白华对中国美学的思想火花,它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令人欣慰的是,学术界最近已注意到这批笔记的价值,并有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相信,通过学术界的挖掘,宗白华的思想会呈现出越来越大的魅力。
尽管宗白华最终没有完成中国美学史的编写工作,给中国当代学术留下了极大的遗憾,但宗白华传留下来的这种严谨求实的学风,却是北京大学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的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宗白华所要求的编写美学史所必需的两个条件,经过宗白华的倡导和他本人的努力,现在已不再是一片空白。其实,宗白华强调做资料整理、具体研究之类的默默无闻的工作,而不急于占领山头,摘取果实,已经透露了一种内在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在经历过那段风风雨雨的历史之后尤为光彩夺目。
来北大以后,宗白华实践了他从德索教授那里学来的美学研究方法,即强调“美学研究不能脱离艺术,不能脱离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不能脱离‘看’和‘听’”。北京有各式各样的艺术展览、大大小小的博物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和保留完好的古典建筑,这些为宗白华的“看”和“听”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宗白华常常拄着拐杖,挤公共汽车进城,饶有兴致地参观展览。就是在北京人看来已经十分平常的一些古典园林建筑中,宗白华也常常能从中看出新的意味,以至于流连忘返,心中充满无限的喜悦。宗白华去世之后,给哲学系留下一大批书籍,这些书大部分是他五六十年代在城里旧书摊上买下的,其中有些外文书现在国外也很难见到。其实宗白华当时并不富裕,平时的衣服上面常常能看见补丁;宗白华挤公共汽车,因为他不愿意把自己关在社会生活之外,在公共汽车上,可以听到社会生活的种种声音,看到社会生活的种种形象,体会到生活里的种种乐趣。
宗白华50年代写了一篇文章,取名为《美学的散步》。宗白华说:“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做‘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中国古代一位影响不小的哲学家——庄子,他好像整天在山野里散步……”“散步”标明了宗白华美学的独特特征。这种特征一方面是方法上的,另一方面是境界上的。从方法上来看,宗白华的美学研究并不局限在抽象的思辨领域。宗白华并不是不知道一般人眼中“散步”所具有的种种弱点,但如果从滞留于一种自由自在的境界来看,这种弱点似乎成了优点。更重要的是,对美学学科而言,“散步”具有某种方法论上的启示。也许宗白华参透了美学的对象拒绝逻辑分析而选择了“散步”,在美学领域里只有“散步”的方法才能接近那玄秘的对象。宗白华“散步”的领域非常广,有常人罕至的地方,也有人多热闹的地方,还有常人不得不身陷其中而不知其乐的地方。就读书来说,古今中外的都喜欢涉猎,尤其喜欢在一些鲜为人知的笔记、杂记中“散步”,也常常能发现一些极有意思的东西。就艺术鉴赏来说,宗白华也有超乎常人想象的胸怀,既景仰古希腊雕刻中的单纯静穆,又迷醉罗丹雕塑中灵与肉的跳动;既赞叹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巧夺天工的技巧,又倾慕印象派大师光与影的交响;既极力尊崇西洋艺术,又无限珍爱中国文化;一方面热爱古典诗词,另一方面又是著名的白话诗人……宗白华对美、艺术的追求与热爱几乎没有时空的界限。宗白华的“散步”不仅局限在狭小的书斋和艺术殿堂里,就是在十分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他也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散步”。宗白华从不计较名利得失,所以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让他特别烦恼。就是在那些非常的日子里,宗白华照样能不惊不惧、无忧无虑。表面上看来,宗白华仿佛“混迹”于平常的生活;实际上,他从没有停止过思考,从不让生活的尘埃沾染那颗晶亮而高贵的心。不仅在个人的精神世界里,而且在与人共同生活的物质世界里,宗白华都能从容悦乐地“散步”,这没有一种极高的觉解是不可能的。只有达到“天地境界”的人,才能如此从容悦乐地“散步”。这话说得并不是十分夸张。哲学系德高望重的张岱年先生在宗白华85寿辰的宴会上,面对众多祝寿者说:“宗白华的人生境界一般人很难达到,至少我没有达到。”
在北大的美学传统中,宗白华占据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从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开始,北大的美学就强调美育,强调读书与做人相结合。按照蔡先生的构想,美学的目的在于“破人我之见,去利害之计较”,“陶养性灵,使之日进于高尚”,也就是说,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宗白华不仅在学问上达到他那个时代的高峰,而且成就了一个完善的人格。不可否认,美学和艺术在宗白华的人格修养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宗白华为北大的美学事业所做的贡献还表现在对后继者的培养上。虽然蔡先生极力提倡美育,也身体力行从事美学教育,但他给北大的美学事业留下的“活的遗产”是有限的,也就是说,蔡先生并没有为北大的美学事业培养出后继队伍。所以在蔡先生之后,北大的美学曾经出现过难以为继的局面。当然这与蔡先生所处的时代的局限有关。在这一点上,宗白华的贡献似乎更大一些。宗白华特别注重对青年教师和学生的培养。早年跟随宗白华的几位助手都深受他的影响。比如,80年代写出在美学界影响极大的《中国小说美学》、《中国美学史大纲》并主编了《现代美学体系》的叶朗教授当年就是宗白华助手之一。从叶教授对中国美学精神的把握和主张融合中西方美学、传统美学和当代美学的胸怀上,都可以看到宗白华的影响。
宗白华的另一位助手于民教授,把他研究春秋时期的审美意识和着重在生活中体验中国美学的奥秘都看作是受到宗白华的启发和引导。美学教研室的另一位教授杨辛先生则深受宗白华重视艺术实践的影响。虽然这些后来者兴趣各不相同,研究的方向也不一致,但在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宗白华的“影子”。而且这些后来者在教学中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宗白华的“影子”留给了下一代的学生。
北大的美学之所以可以称得上一个学派,不仅因为它有一群有影响的学者和延续不断的学术传统,更重要的是它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尤其是从整个中国现当代的学术背景的角度来看,它的特点更加鲜明。整个中国当代学术,有一种生硬地套用西方学术的范畴系统的倾向,充斥着唯心唯物的争论。但北大的美学,尤其是中国传统美学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没有受到什么外在的东西的冲击。其实北大的美学也特别强调对西方美学的合理吸收,但这种吸收从来就不是生搬硬套,尤其是在宗白华那里,中西美学的融合完全做到了不露痕迹。更具体地说,北大美学在方法和胸怀上强调中西比较、对话、沟通与融合,但它的理论内核是中国传统美学,尤其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意象和意境理论。北大的美学基本上是从这个理论基石上生发、拓展开来的。从朱光潜的《诗论》、宗白华的《中国艺术意境的诞生》到叶朗的《现代美学体系》,可以看到这个以意象为中心的美学理论的不断的向前推进,不断的丰满和完善。随着北大美学学派建设的发展,宗白华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似乎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重大了。这不仅表现在他特有的人格魅力和对后继者的培养上,更主要地表现在他对这个学派的理论核心的建设上。
在当代中国美学寻求理论发展和突破的阵痛中,人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宗白华,回到宗白华博大的理论胸怀,回到宗白华对中国美学的精深的洞察,回到宗白华由艺术和美学而成就的完美的人格。
中国古代美学与西欧古代以来的美学相较而言是零散的、不够体系化、也不够哲学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美学就没有自己的特色,而是意味着凭借某种特殊方式的介入才能将其挖掘出来而不至于隔靴挠痒,这种特殊方式其实正是一种召唤:生命的灵光。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也许正是这种“生命对学术的感应”。“学术”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知”,即能广涉多方而显得博,这个层次也可以成为大家,但终会显得薄;第二个层次是“信”,即把学术上升为可引领实践的信仰,这时的学问已不再是学问,而是人生,这才会显得厚,这种学术里出的大家已是艺术家,如尼采等。
刘小枫总结:“作为美学家,宗白华的基本立场是探寻使人生的生活成为艺术品似的创造……在宗白华那里,艺术问题首先是人生问题,艺术是一种人生观,‘艺术式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中出现的频率最多的词就是:宇宙、人生、艺术、美、心灵、节奏、旋律、飞舞、音乐化、体验。这些词语既解释了中国艺术的至境,也显现出揭示者的人生至境。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同样,想象一种艺术(更何况还是“体认”这种艺术,再者,艺术也是一种“语言形式”),也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宗白华选择了一种“纯粹”的中国艺术,也就塑造了一种淡泊、灵启式的生活方式。也许,要想体验到中国艺术至境的乐趣,宗白华的选择是惟一的,但是,世界上的艺术是多姿多彩的,因此人生也应是多元化的,何况,人生的至境也还有其他几种。中国古代美学遇到宗白华真可谓是一种幸运,因为他学贯中西,跳出来又扎进去,这猛子才扎得深。也正是在宗白华的文章里,中国美学的各方特色被熔炼出来并被标举到了极致。也许在他之前也曾有人发掘过,但都不可能像他那样贯入一种极其深沉挚厚的生命意识,这一点或许是得益于他曾深究过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生命哲学。
中国哲学、中国诗画中的空间意识和中国艺术中的典型精神,被宗白华融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问题:一阴一阳谓之道趋向音乐境界,渗透时间节奏书法中的飞舞;其实都体现着一种精神:人的悟道、道合人生,个体生命与无穷宇宙的相应相生。
可以说,宗白华把中国体验美学推向了极致,后人很难再出其右,他作为一个审美悟道者本身已成为一种道显而美的象征。但还应藉着散步者的灵光走进茫茫天地之间去不断求索。
宗白华的诗
流云小诗(选登)
夜
一时间
觉得我的微躯
是一颗小星,
莹然万星里
随着星流。
一会儿
又觉着我的心
是一张明镜,
宇宙的万星
在里面灿着。
晨
夜将去。
晓色来。
清冷的蓝光
进披几席。
剩残的夜影
遁居墙阴。
现实展开了。
空间呈现了。
森罗的世界
又笼罩了脆弱的孤心!
飞蛾
一切群生中
我颂扬投火的飞蛾!
唯有他,
得着了光明中伟大的死!
问祖国
祖国!祖国!
你这样灿烂明丽的河山
怎蒙了漫天无际的黑雾?
你这样聪慧多才的民族
怎堕入长梦不醒的迷途
你沉雾几时消?
你长梦几时寤?
我在此独立苍茫
你对我默然无语!
诗
啊,诗从何处寻?
在细雨下,点碎花花声!
在微风里,飘来流水音!
在蓝空天末,摇摇欲坠的孤星!
系住
那含羞伏案时
回眸的一粲,
永远地系住了我
横流四海的放心。
红花
我立在光的泉上。
眼看滟滟的波,流到人间。
我随手掷下红花一朵,
人间添了一分春色。
冬
莹白的雪
深黄的叶
盖住了宇宙的心。
但是,我的朋友,
我知道你心中的热烈
在孕育着明春之花
彩虹
彩虹一弓
艳绝天地。
我欲造一句之诗,
表现人生。
人生
理性的光
情绪的海
白云流空,
便是思想片片。
是自然伟大么?
是人生伟大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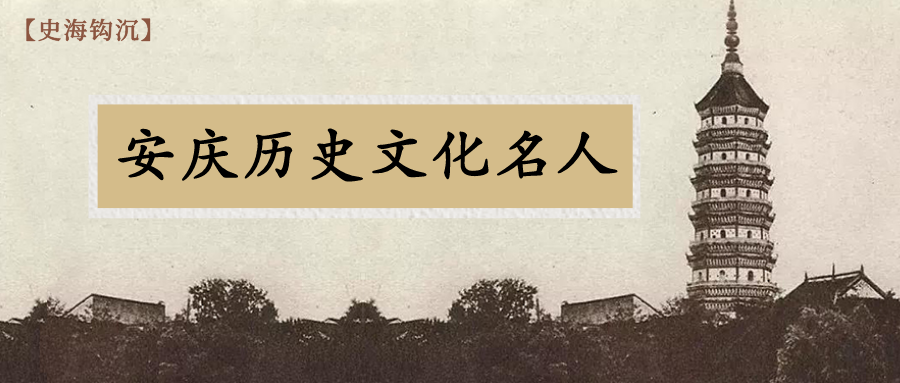
 皖公网安备34080302000118号
皖公网安备34080302000118号